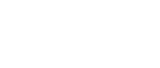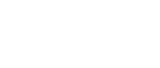【城记】煤炭坝:一座城的“浴火重生”
| 招商动态 |2017-03-12
煤炭坝五亩冲矿 摄影/金林
深入荒芜的矿区已非首次。
上一次,是宜章梅田煤矿,在一个萧索的秋天。
3月,进入煤炭坝矿区,野花在废弃的矿区遍地盛开,那留存下来的亮丽黑色,彰显着这里曾有过的热闹。
被遗弃的矿区,像是被时代巨轮碾压过后的废墟,矿工们像车轮勾带出的细泥,从矿井里走到地上,告别集体,重新成为孑然一身的个体,努力谋求生计。
“百年煤城”煤炭坝不过是湖南煤矿城镇的一个缩影。这个曾被称为“小香港”的小镇,习惯了熙攘、鼎沸的人群,习惯了12点才开始的夜生活……小镇不甘寂寞,人们的身体里也同样刻下商业与工业的因子。湘中门都、煤矿遗址公园,工业与旅游,依旧是煤炭坝的复兴之路。小镇始终相信,那些曾经失落、散去的辉煌,终究会回到这里。
废弃的斜井人车,矿工坐在车上进入井下。 图/金林
煤炭坝
,一个与“煤炭生产”再无关系的小镇
它离长沙仅70公里,在史册里有五百年。
从元末明初,它被人们发现起,作为“湘中煤都”的生命已经开启了倒计时。
即使,它曾经“掏心掏肺”将光明和温暖带给三湘大地,贡献了一个县城三分之一的财税收入,为5万多人提供衣食住行,甚至曾被称作湖南的“小香港”。但如同所有资源型小镇一样,产业转型依然是它最终的归宿,这每个人都心知肚明。
然而,当2014年底,千万矿工走过的井口被水泥砖块封堵时,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。
对于一个小镇来说,这不过是史册中的一笔,是时代洪流中一片浪花。然而,这轻轻一笔落在每一个人身上,是扎扎实实的人生。
人们不得不告别和离开,告别一份职业、一个圈子、一段岁月,留下的是青春、故事以及传说。
《煤炭坝煤矿志》内文截图
煤炭坝,位于桃江、益阳、宁乡三县的交界地。
如果时光可以回转,你有幸能走进多年前的矿工宿舍,你会听到湖南各地的口音。说“吃米面”的是常德人,说“一嘎几(怎么了)”的是宁乡人,喜欢用去声开腔的是益阳人。
来自不同地域的矿工们住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。下井前,大家还能区分谁是谁。从深达几百米的井下走出来时,所有人都换成了同一个“肤色”。煤灰遮蔽了所有人的脸,只有白色的眼白和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矿区有公共澡堂,摘掉矿帽,脱去工装,往池子里一钻,洗去煤灰后,彼此赤诚相见。家属楼就在矿区,工友的妻子们也彼此认识,忘记买米,少个油,敲敲邻居家的门就好。矿区还有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工友们的孩子成了同班同学。成年后,他乡再遇,攀谈几句,总会问,“喂,你爸叫什么?搞不好跟我爸是一个队的。”
矿区还有食堂,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五亩冲的酸菜馅包子,给你带了几个。”去食堂的路上,总会见到有人捧着黄色的瓷盆,盛满一家人的米饭,跑回家去。“食堂的饭好便宜,我打了好大一盆。”
矿区的自来水是不要钱的,虽然有时候早上打开水龙头,会冒出黄泥水,但似乎没太多人抱怨,将水盛在盆里,沉淀沉淀,依然能用。
矿区的“煤城商店”里有7毛5的湘南烟、1块钱的长沙烟和8毛的常德银象烟卖。出井下班,还未来得及脱下沾满煤灰的工装,三三两两地斜倚在玻璃柜台前,用沾满煤灰的手,从裤袋子里掏出一包烟,点燃,再眯着眼睛,深吸一口。 煤灰掉在商店的地板上,粘在玻璃柜台上,没有人嫌弃。
那是一个国有企业可以包办员工“生老病死”的年代,如今已成绝唱。2014年,对于煤炭坝来说,是历史的转折点。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来说,是生活的转折点。
曾经人声鼎沸的工人村,只剩下零星的几户人家,热闹的是几只母鸡扑扇翅膀咯咯的叫声。没有铁轨的铁路被野草淹没,斑驳的矿车在时光里腐朽,杂草丛里不知道谁掉落了“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”。
墙壁上还贴着“为了家庭,我今天一定按章操作,绝不违章”的安全誓词。
一切仿佛刚刚停顿,仿佛第二天,还会有人戴着矿灯,打开铁门,拉动井口的铁索,开始一天新的工作。但偌大的矿区,只有看家的狗,四处奔跑,不吠也不叫。
幸运的是,离开了矿区的人们,在县城再次相聚。
他们住在同一个安置小区里,虽然没有了公共澡堂、食堂和不要钱的自来水,但幸好还有那一群人。总有人,搬一把木凳,一坐就是一下午,来往过路招呼不断。有时候,门也懒得关,邻居串门方便。小区里的保洁员就是以前的工友,路过身旁,拍拍肩膀,递根烟。
从此,“煤炭”二字只存在了地名中,但人走去了远方。
3月1日,湖湘地理寻访这个曾经的“小香港”,“煤城”的标牌、镇口铁制的煤矿机械提醒着我们进入了一座百年煤城;而正在生产的门业园和硕大的“湘中门都”的标识,又似乎昭示着煤炭坝的未来。
“湘中门都”的标识 摄影/金林
运煤
车一排就是好几公里
镇上并没有想象中的萧条,或许只有经历了繁华的煤炭坝人,才会不习惯这份宁静。
“以前可热闹了,夜生活12点才开始呢,现在矿工都搬走了。”我们入住的酒店开在煤炭坝曾经最繁华的地段,服务员向我们热情介绍时,我这才注意到街边那些已经关闭还没来得及拆除招牌的KTV、已经停业的高级酒店、酒店门口停车场执着吆喝的几个擦鞋妇人……
1895年,湖南矿务总局在煤炭坝开矿,开启了煤炭坝的百年煤城的序幕。2000年以前,煤炭一直是宁乡的支柱产业,小小的煤炭坝里,住有5万多人。
2014年底,煤矿关停,矿工们陆续搬离了这个小镇。54岁的罗文乾(化名)是我那天傍晚在沙子坡遇到的第一个矿工,沙子坡曾经是矿工的聚居地,低矮的前苏联样式房屋,一块空地是以前的灯光球场,稍显寥落。
“最鼎盛的时候,五亩冲煤矿前每天等着拖煤的车,一直从五亩冲排到竹山塘,好几公里。”他说的鼎盛期并不十分遥远,2010年左右还出现过这样的场景。
“以前上学不要钱,住房不要钱,水不要钱,电一个月才两毛。”絮叨里,是他对于曾经的“好日子”的怀念。1982年,罗文乾顶了父亲的班,在五亩冲煤矿当采掘工,每个月工资35.5元钱。
五亩冲煤矿大门 摄影/金林
“第一次下井,很兴奋,300多斤的刮板一个人背。有时还义务加班几个小时。”罗文乾在煤矿工人“为祖国做贡献”的口号声中长大,对于矿井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
“下井前吃个五亩冲的包子,酸菜馅最好吃。上了井泡个澡,骑着自行车到处跑,晚上可以看电影……”他开始兴奋起来,在他的回忆里,劳动的艰辛和危险被过滤掉了,只剩下最美好的东西。1991年,他和几个工友一同停薪留职,下了海,到长沙学做饼干,“去了三个人,他们学了几个月就回来做,后来都没有做起来,我学了一年,做饼干看起来容易,其实里面有很多学问呢。”回来后,罗文乾在沙子坡开了家饼干店,“一个月就赚了700块钱。”靠着饼干生意,他在沙子坡建起了新房。
居民房,只有零星的住户 摄影/金林
“那
时候真叫衣锦还乡了”
竹山塘矿区是最早开发旅游的一个矿区,通往矿区的路上竖着不少旅游指示牌,矿区内原本锈迹斑斑的机械、水塔被涂上了颜色,房子经过了修葺、装修,汽车影院已经开张,被封堵的井口“2014年11月20日封”几个字鲜红醒目。
66岁的莫国清已搬到了宁乡县城,3月2日,他回到竹山塘照看自家菜地,每隔一段时间,他会回到竹山塘住上几天,采摘些新鲜蔬菜回去。1973年,他从桃江招工进入煤矿,“12月来的,那时候我结婚才几天。”在宁乡40多年,依旧带着乡音。“那时候一个公社就招了三个人,我是其中一个。”
“有两个和我一批过来的年轻人,下了一次井,就因为害怕回去了。”莫国清最初是当采掘工,“扛着百来斤的钻机,上了井,手都抬不起来。”不过相比于矿井里的辛苦,莫国清更享受穿着工装回乡时带来的羡慕眼光,“那时候真叫衣锦还乡了。”他揉揉曾在井下作业时受伤的拇指说。
煤矿关停之后,像莫国清一样的矿工,大部分都搬到了县城住。而有一群矿工,却没有远离煤炭坝,他们依旧每天训练。
矿山救援队是矿区唯一保留下来的队伍,只是现在门前挂了四块牌,“长沙市矿山应急救援基地”“宁乡县阳光应急救援基地”“煤炭坝镇政府专职消防队”“长沙市矿山救援队轨道交通应急救援基地”。他们经常参加全省矿区救援,也负责煤炭坝镇的消防和交通事故救援。
“就是要胆大,自己都害怕,还怎么救人呢?”救援队的队长谢四明身材魁梧,笑起来却有些憨厚。他原本是西峰仑矿的一线采煤工,1984年加入了救援队,“当时救援队的队长问我怕死人吗,我说,不怕。”
3月2日,矿山救援队队长谢四明特意穿上救援队的服装,站在已封闭的竹山塘矿井前。摄影/金林
“今
天去饭店吃饭,都坐满了”
煤矿注定成为过去,不过它们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出现。
竹山塘矿区是最早开发建设的矿区,竹山塘的汽车影院已经开张,负责人任泉是宁乡县城人,在各地考察了汽车影院,终于决定回到宁乡,选择了竹山塘创业,“这煤坪刚好是个阶梯广场。”
汽车影院 摄影/金林
在竹山塘煤矿的未来规划里,它将是个类似于北京798的创艺园,宁乡籍的画家成五一的工作室就在这里,被封禁的矿井也将再次开放,作为采矿体验项目。
成五一工作室 摄影/金林
五亩冲创客园则将成为美术学生的实践写生教育基地;西峰仑创展园,会成为类似于宜家家居博览的创展公园;宁乡传统小吃美食则会集中在跃进煤矿创味园。
其实在煤炭坝关停煤矿之前,转型早已经开始,煤炭坝的人们相信“湘中门都”将会替代百年煤城,让煤炭坝再次辉煌。
“今天去饭店吃饭,都坐满了。”3月2日下午,煤炭坝招商办的黄军来到办公室,神情兴奋,他负责煤炭坝门业园的招商引资,饭店里满座的场景让他似乎看到了煤炭坝的未来。
“之前也进行过其他的探索,花炮厂、电子厂等,花炮厂不能集群,电子厂已经是夕阳产业。都没有发展起来。”在全国各地的奔走考察中,煤炭坝最终确定了做门业,“那时刚好长沙黎圫的门业要集体搬迁。”如今入驻煤炭坝门业园的门企已经有80多家。2012年,曾经一天签下了11家门企,“对面的酒店好像也有人要重新开张了。”他点起一支烟,兴奋地说。
矿区内,一棵与房屋“共生”的树,根系扎进了砖缝,从此树成了墙,墙成了根。摄影/金林
“煤矿兴盛的时候,煤的买卖中间都有黄牛党。天天排起长队,但是煤矿是有限的,肯定会被采完的。”曾经的煤老板贺凯良,依旧保持着在矿区的某些习惯,比如,仍不习惯穿浅色的衣服,“以前在矿区,每天一脸的灰,早上去办公室,桌上一定是一层灰。”他曾是历史上煤炭坝最年轻的矿长,22岁就成了乡镇煤矿矿长,后来承包了贺家桥煤矿。
“煤炭市场是波动的。”他用手做一个起伏的动作说,“而且得担心安全问题啊。”他于2006年开始投资花炮厂,2011年,他创办了三彩油墨,不过煤炭坝煤老板转型在当地办实业的并不多,“煤炭坝有人力资源,从煤矿下来的煤炭工人;玉煤大道拉通了,交通也便利;作为一个工业城镇,它有商业氛围,人们容易接受企业……”他条理清晰地数着煤炭坝的优势,下一步,他准备试水门业。
煤炭坝人侧记
小区里住的都是矿区的人
每个人都好像在哪里见过
3月3日下午,家住宁乡县城的赵世英准备出门散步,从家到小区门口,一路招呼过去,散步的队伍就变成了三个。
“我想在那种点菜,但不允许。”走到小区门口,赵世英指着门前的一块空地说,她在五亩冲还有几块菜地,那天丈夫回了五亩冲,照看菜地。她所住的小区,住户多是煤炭坝矿区的人,“她们在五亩冲就跟我是邻居,现在我住2栋,她们住3栋。”赵世英介绍她的同伴。
赵世英是常德人,1986年随丈夫入户到煤炭坝五亩冲煤矿,在矿区食堂工作。“两个孩子都没当煤炭工人,读书出去了。”她不无骄傲地说,在煤矿关停之后,她在长沙给儿子带孩子,去年决定回县城来住,“在矿区的时候大家就都认识,一起看电影,串门喝茶,到了这里也是一样,都不用关门的,招呼一声,就可以组个局,散步也好,打牌也可以。”
小区的清洁工刘辉(化名)也是这里的住户,他见证了五亩冲煤矿的关停,“2014年11月20日嘛,当天的物料都放下去了,没想到停电了,然后直接停产了。”扫着地,后面有人过来拍拍他的脑袋,回头原来是老工友,递上支烟,又聊开去了。
84岁的陈如钦也是煤炭坝的老矿工,经历了用肩挑煤的艰苦时代,坐在小区门口的花坛上,不时有人坐下来跟他聊聊天,只是,人已离开,陈如钦还没想起那个人是谁,只是觉得在哪里见过。
 招商热线:400-151-2002
招商热线:400-151-2002